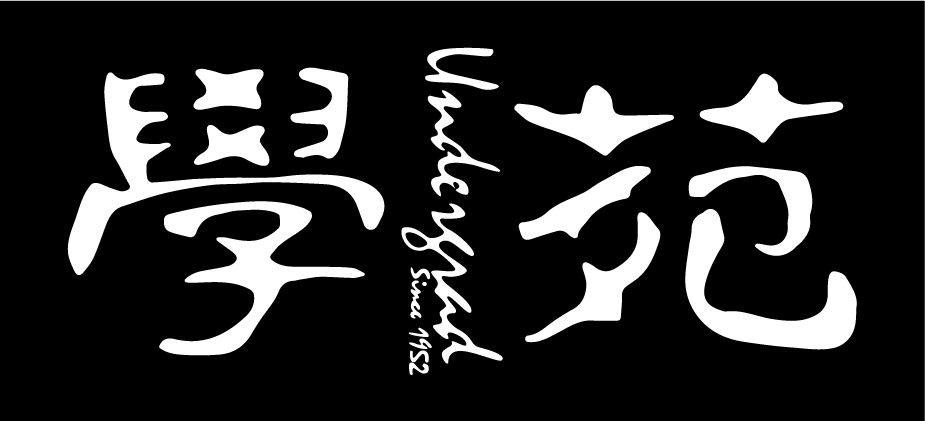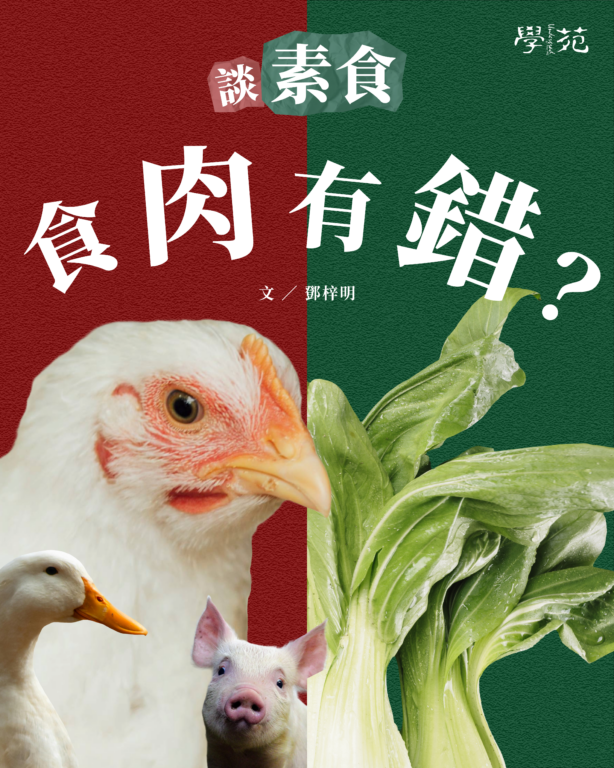
文/去屆編輯 鄧梓明
香港近年有不少關於動物的大新聞。
2021年11月9日,漁護署開始定期捕殺市區野豬,輿論譁然。漁護署解釋,這是因為原有「捕捉、絕育/避孕、放回」方案成效不彰,近年野豬傷人或滋擾個案大增。
2023年7月初,一週內有三匹馬葬身馬場:一匹因斷腳被人道毀滅,兩匹暴斃賽場。一週後,西貢水域出現一條長約7米的布氏鯨,吸引大批市民出海觀鯨。7月31日早上傳來鯨魚死訊。解剖報告指出,布氏鯨是被一艘快速行駛的船隻撞擊而亡。政府大受抨擊,被指海岸保護區數量不足,當局發現鯨蹤後亦未有設「禁船區」。漁護署其後承諾檢視法例,今年3月再透露年內會就立法諮詢公眾,諮詢內容暫擬包括賦予政府權力限制船隻航行及賦予《觀豚守則》法定地位。
我們能否抓緊這些惻隱的瞬間,看見自己對動物的剝削?看看我們的餐桌,每年有約800億隻陸地動物被屠宰食用。如果我們不應該吃狗肉,我們何以稱自己可以吃養殖場裏的豬雞牛羊?如果你也曾經被笑問「拖拉機壓死的老鼠點計?」除了翻一個白眼,說這是不得已的犧牲,我們能不能有更認真的答案?

在本文上半部分,我們先嘗試思考第一個問題:食肉有錯嗎?
哲學家Peter Singer以偏好效益主義論證我們應純素飲食。他主張考慮行為對世上所有有感知能力的生物之「偏好」所造成的影響,來判斷行為是否道德。使世上最多偏好得以滿足的行為便是道德的,而計算利弊時,任何人或動物的偏好都應一視同仁。在工廠式養殖場中,以不人道的方法飼養和屠宰動物,雖然滿足我們自己的瑣碎偏好(口腹之欲),但犧牲了動物最重要的偏好(免於痛苦的欲望和求生欲),因此是不道德的,所以他認為我們有道德責任成為素食者。
自然權利理論家Tom Regan質疑Singer的計算未必得出養殖場不道德的結論。不少人非常享受品嚐肉食,更有極多人依賴畜牧業為生,例如屠夫、飼料商、食品包裝商、運輸商等;若無人吃肉,這些行業將遭受重擊。正是因此,我們其實無從估計素食是否最能滿足所有人和動物的偏好。另外,功利主義以世上快樂之和判定道德,本身也帶來可怕的結論:若殺死一個無辜者最能滿足世上的偏好,這也會成為我們的道德責任嗎?Regan指出,會出現這個荒謬的境況正因功利主義忽略了生命本身的價值——人或動物的權利乃歸因於其生命本身,而非偏好的加減算術。
Regan提出生命主體(subject of a life)的概念,意指具有信念、欲望、感知、記憶、對未來的意識、追求欲望與目標的能力、自我意識、經驗快樂痛苦的能力的生命。一般而言,一歲以上精神正常的哺乳動物都符合上述生命主體之條件。生命主體能過一個有自主意識的生活,因此擁有「固有價值」,而該固有價值與Singer重視的偏好和欲望無關。Regan將生命比喻成杯子、生命的經驗作液體。若Singer認為注入杯子的液體(經歷、對偏好的滿足)有價值,Regan則認為生命不只是裝載經驗的容器,杯子(生命主體)本身就有價值。倘若我們繁殖、宰殺動物食用,將動物視為人類的工具,正是無視了動物的固有價值,違反動物作為生命主體的權利。
動物權利引來不少質疑,例如哲學家Mary Anne Warren指出,我們在應對動物帶來的威脅(如鼠患)時,往往更輕易殺死動物,這正說明我們會以理性能力區分人類和其他動物。比起人類,沒有理性思考能力的動物只有很低程度的權利,Warren認為人類為了營養、文化或宗教的原因吃肉,已足以凌駕動物的生存權。不過,現時我們對動物的差別對待隨處可見,與其以此證明動物道德權利不如人,甚至佐證肉食工業的合理性,或者我們更應反思現時對待動物的方式,以及當中隱含的對其他物種的歧視。
哲學家Carl Cohen更反駁,動物不能作道德判斷,因此沒有權利可言。同樣不能作道德判斷的人類(如嬰兒)則因屬於普遍有道德能力的人類族群而可享有權利。雖然動物沒有權利,但人有人道對待動物之義務,避免施加不必要的痛苦。Cohen認為只要以人道方法養殖和屠宰動物,便沒有道德問題。不過,Cohen同樣引來諸多質疑:為何不能思考道德便沒有道德權利?雖然多數人有道德判斷能力,但權利為何是建基於族群多數,而非個體情況?如果說只有人類有道德判斷能力,這個族群劃界卻是主觀的,我們完全可以收窄或拓寬道德族群定義:只有「8歲以上的人」或「哺乳類動物」有道德能力。如何為族群劃邊界?
除了效益主義論和自然權利論,亦有其他動物權利理論建基於德性倫理、痛覺主義、女性主義等。其中女性主義理論重視情感,批評傳統動物倫理過分理性,把情感排拒於道德思考之外。有趣的是,不少對動物的理性思考實亦源自對動物的感性關懷。Regan曾指「一方面是甘地的生活和思想,另一方面是一個四足犬朋友的生與死——一個頭腦和心靈的經典結合——引導了我問有關我吃的食物的道德問題。」當我們從道德哲學中尋找權利之定義,也許最終要回到我們關懷動物的初衷:對逝去的伴侶動物的記憶、對某一段影片中的某一個動物的惻隱,接下來的理性思考才不會跌入真空。

上文淺談動物倫理,為素食提供理論基礎。但倫理之後是現實——沒有完美的素食,現代農業正傷害無數動物。我們應如何面對現實?
農牧業是砍伐森林的主因,導致動物死傷無數。研究顯示,2011至2015年間,世界各地每年因發展農牧業而被砍伐的熱帶森林達數百萬公頃。當中約一半土地因種種原因荒廢,實際用於農牧業的土地中,畜牧業和農業各佔約一半。森林被砍伐後,動物頓失家園,部份受傷致死,倖存的動物遷徙異地,但往往難以適應新的生態環境。世界自然基金會澳洲分會估計,2005年至2015年,新南威爾士的森林砍伐每年導致近五百萬動物死亡。
當然,還有無數田間動物被農夫殺死。殺蟲劑和鼠藥除了殺死無數蛇蟲鼠蟻,亦會殃及其他野生動物,例如有學者估算,在加拿大,每年約二百七十萬隻雀鳥被農藥殺死。美國政府亦統計,1961至1975年,當地至少有二千萬條魚因農藥與化肥污染死亡。無數田間動物被耕耘機、除草機、收割機等大型農作機器輾壓、絞殺,野生動物覓食時亦會被農場柵欄和電網纏住或電死,或被農夫殺死。
2018年,BBC喜劇問答節目QI曾問參加者:請問在牛油果、杏仁、蜜瓜、奇異果和胡桃南瓜之中,嚴格的純素主義者會吃哪一個?主持人揭曉:五種食物全都不是「純素」,因為農夫會召養蜂人運來蜜蜂授粉,類似的蔬果還有西蘭花、車厘子、青瓜等。研究顯示,在107種依賴動物授粉的常見農產品中,缺乏動物授粉會顯著減少其中70種的產量。若這些蔬果的農場附近沒有足夠蜜蜂,農夫便會請來養蜂人,倘當地蜜蜂供不應求,更要從外地運來蜜蜂。長途運輸影響蜜蜂免疫力,到埗後亦可能會與當地蜜蜂交叉傳染;授粉蜜蜂會接觸更多農藥,影響免疫力。
哲學家Donald Bruckner因而提出,動物權益並不是要求人們食素,而是在拒絕消費工廠養殖場生產的動物產品之餘,也盡量尋找其他食物來源,減少購買大型農場生產的蔬果。Bruckner指,順倫理素食主義的思路,我們有責任食用死於車禍的動物,甚至可能有責任食用野果、垃圾箱中未變質的食物、務農時殺死的田間動物,以取代消費農場產品。有人亦提倡自己種菜或購買社區農場的蔬果,多吃昆蟲、貝殼等或許無法感知痛覺的動物,甚至吃無痛死亡的放牧動物,減少消費傳統農產品。總之,素食絕不完美,若我們想完全尊重動物權益,似乎只能脫離消費,成為拾荒者。

哲學家Lori Gruen 和Robert C. Jones進而提倡視素食主義為一種願景——承認人的生存必然意味著殺死有感知的生命、承認不傷害動物權益的素食主義在現實中難以實現。如此,素食主義才有更大的意義:我們真正認識到個人的道德責任,真誠地承認我們為動物帶來的苦難,嘗試接納我們的不完美,然後選擇自己的消費方式。我們面前的選項不是食肉、蛋奶素或純素,而是我們願意為減輕他者的苦難而犧牲多少,我們在這個以動物的苦難砌成的社會中願意參與幾多、抽身幾多。
視純素為不可能的願景,才能想像可實踐的素食主義。理想的農業可以是什麼樣子?一個完全不剝削動物的農業是否可能?我們可以發展農業技術,減少對動物傷害。例如在美洲國家頗為流行的免耕農法可減少使用耕耘機、新型老鼠藥可為老鼠絕育,而為保護鳥類,不少劇毒農藥已被禁止。不過,即使未來耕作可以完全無害,如果我們繼續大規模毀林佔地,無害農業可以從何談起?
哲學家Josh Milburn認為,新興的垂直農業將是無害農業的理想模式。垂直農業將農業搬到室內,精準檢測燈光、濕度等,多採用無土栽培。其中「氣耕」將作物懸掛空中,使作物吸收營養霧氣;「水耕」將作物根部浸泡在營養液中,或將營養液滴在作物根部。這些作物多種植在密密麻麻的層架上,加上建築可有多個樓層,節省空間。倘於市區建立垂直農場,使農場靠近消費者,更能大幅降低食物冷藏和運輸的成本。由於室內農場密封,進入垂直農場前甚至要全身消毒,所以室內沒有蛇蟲鼠蟻,耕作過程不會直接傷害動物;授粉機器人更已在近年打入農業市場。倘若未來農業完全轉型至高效的垂直農場,不但不需毀林佔地,更可釋放農地,回歸自然。
不過,因其高昂成本,垂直農業在可見的將來都不能完全取代傳統農業。曾有研究估算垂直農場和傳統農場種植生菜的平均成本,發現雖然垂直農場用水成本不及傳統農場一成,但節省的成本不多;垂直農業的兩項主要成本是能源(約三成)和勞動力(約七成),總成本比傳統農業高逾一倍。正因生產成本高昂,垂直農業現時只種植生長期短的貴價蔬果,例如綠葉菜、莓果、番茄等;種植大米、小麥等主糧則難以盈利。
我們能為上述問題找到解決方法嗎?或許。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只能是不完美的素食者,一直在傷害幾多、如何傷害的問題前徘徊。這不是問題,因為純素是種願景——純素飲食屬於未來。但這不是我們停步的藉口,願我們仍有勇氣問自己願意為減輕他者的苦難而犧牲幾多、犧牲什麼,然後真誠地嘗試。
【編按:本文原定於二零二三、二零二四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輯委員會任內出版,惟因編輯自身能力不足而未竟。敝編委會邀請去屆編輯續筆完稿並予刊載,冀此能成引玉之磚,為社會思潮添一磚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