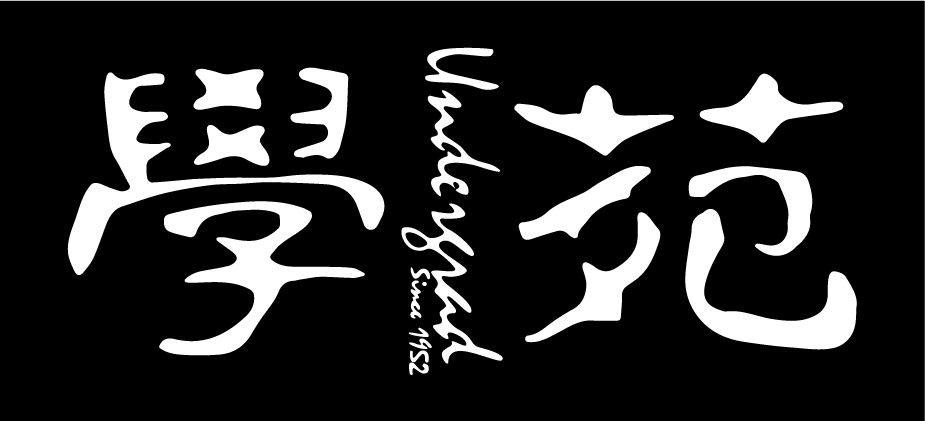大提琴琴音一落,演奏廳一片掌聲雷動,當然亦少不了觀眾Bravo的喝彩聲。文化中心的古典樂迷素來熱情,指揮家、獨奏者不從後台出來謝幕三四遍,掌聲也絕不罷休。那晚台上,站著接受喝彩的是本地大提琴家李垂誼,下半場演的是德伏扎克的大提琴協奏曲,伴奏的是港樂。
上半場觀眾一如既往拍案叫絕。上半場的節目全是中國音樂,民歌、移植作品、中國作曲家的管弦樂作品一應俱全。所選的,對學習中國音樂者而言,乃耳熟能詳司空見慣之作。台上響著的雲南民歌《對調》要視奏(sight-reading)易如反掌,還有緊接下來的移植二胡名曲《二泉映月》、民族風格管弦樂的經典《瑤族舞曲》都稱不上是高難度的作品,惟港樂的演譯別樹一幟自成一家。比如說,《對調》的ti音(按:sol-fa name)奏起來就是要偏低一點,才有雲南的風土味,但本地最佳的職業樂團似乎生怕觀眾誤會自己走音失誤;餘下曲目的演奏亦非常西化。中國音樂難在意境、民族或戲曲的風格的掌握,而非填寫在譜上密密麻麻的音符。輕視中國音樂之難,換來就是一場畫龍而不點睛的演出。
香港的演奏廳向來重西洋輕中國,觀乎歷年藝術節節目,管弦樂定必佔多數且是重金禮聘回來(例如今年邀得古典樂壇炙手可熱的年輕指揮家杜達美Gustavo Dudamel),而中樂則必為香港中樂團。大概是香港人崇洋,沉醉於馬勒對人生豐富而立體的思考或是莫札特優雅又活潑的樂章而不能自拔,無法抽離如斯畸型的發展模式。現代中國音樂的寫作吸納大量西方的理論與元素,保留民族特色之餘,亦富有時代感,例如二胡協奏曲《藍色星球》似乎是對霍爾斯特(Gustav Holst)的《行星組曲》致敬、王建民多首的二胡狂想曲皆是現代風格的少數民族音樂。西方作曲家甚至開始以中樂團作為作品的媒介,好其富神秘感和別樹一幟的音色和音響效果。社會對中國音樂根深蒂固的印象雖非盡錯,但幾乎可肯定已經與現代中樂發展嚴重脫節。
西方管弦樂隊按譜面演奏中國音樂是一個通病,外國樂隊受制於文化隔閡尚情有可原,惟以華人作骨幹的港樂實難辭其咎。現代音樂的發展已不再局限於單一地域,除了移植樂曲,更多是中國作曲家譜寫予管弦樂隊的作品,《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為其中一首最被廣泛演奏和灌錄的中國風格樂曲,甚至是中西融合的作品,如趙季平以中樂隊伴奏的大提琴協奏曲《莊周夢》,剖析莊周夢蝶的懷疑論思想,亦大行其道。比利時大提琴家Marrie Hallynck正是令人敬佩的範例,她與香港中樂團合作演奏《莊周夢》,以琴弓劃破了文化的隔膜,克服難以掌握的中國風格,雖然進步空間仍在,但仍獲一致好評,向世界展示中西音樂交融的火花。
香港乃中西文化交匯之地,盡得發展這類型音樂的地利,面對中西音樂交流愈趨頻繁的時代,演奏者作為現代作品與觀眾之間的橋樑,必須摒棄唯西樂獨尊的心態,認真看待中國音樂。古典音樂固為本業,但本地管弦樂發展絕不能自滿於演奏華格納、馬勒、與布魯克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