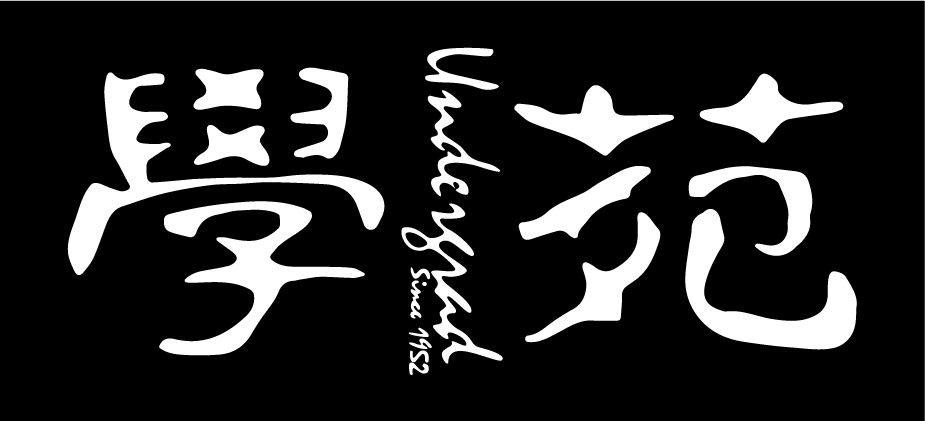文/譚天悅
從九月二十六日開始,一個個撐著雨傘的香港人開始在不同角落裡,綻開一朵朵自由的花朵。這七十九天,喚醒了無數港人對爭取普選的渴求,也突破了香港人對藝術的冷感,擴闊藝術空間從博物館到街頭。每個藝術品,反映了佔領區的各種特色,也同時融合了街頭特色和真普選訴求。從一開始抗爭模式的改變,已印證香港社會運動的轉化,因抗爭而生的藝術品也就這樣遍地開花。這一場啟蒙時代,現在才正式開始。
對不少香港人來說,在二零一四年九月前,政治和藝術可是兩種遙不可及的概念。在政治上,無論回歸前後,我們雖為合資格的香港選民,但從來沒有機會使用我們的一票,選出真正屬於香港人的特首。另外,在特區政府的「大力推廣」之下,多少藝術最後淪為商品化,存放在博物館和藝廊的高閣上。西九文化管理區多年只聞樓梯響,任由土地凋零在一角。政策的失衡、行人的疏離,和城市的混亂成為香港的常態。但從佔領開始後,香港人敢於以自己的雙腳,表達我們對人大落閘的不滿;在佔領區地上,用我們的雙手,創作出既能展示公民抗命,又不失地區特色的藝術品。
相對以往香港社會運動的模式,雨傘運動出現了新的突破。在方式上,它是一場佔領,而佔據的場所,竟然在平常人流如鯽的馬路和天橋上。佔領區中各有特色,金鐘人流最多,旺角變化最大,而銅鑼灣相對較為平靜。在組織上,從罷課開始,運動由年輕人主導。有別於「集會、喊口號、唱歌、散會」的社運常態,雨傘運動流動性強,加上有不同佔領區,藝術展示變得更接近群眾,擺放時間越長,越能幫助藝術品融入整個佔領區,也越鼓勵佔領者與藝術品接觸、交流。對一場社運來說,精神象徵有助連結參與者,如果八九民運的記號是民主女神,反服貿學運的符號是太陽花,那麼從二零一四年九月廿八日開始,香港人心中也有一把雨傘。
金鐘 - 撐起雨傘
作為佔領運動的第一據點,金鐘除了是「大台」所在,警方的嚴密佈防更令人每天人心惶惶。九月,我們曾於金鐘立法會門外、龍和道和夏慤道手拿著雨傘和戴著口罩,嘗試以我們單薄的身軀,對抗警方無情的暴力。就這樣,雨傘成為我們最好的標誌,亦衍生不同的藝術靈感。不論你是專業藝術家,藝術學生,還是毫無藝術經驗的佔領者,只要你有話想說,金鐘的天橋、洗手間和馬路提供了機會,打破藝術只在博物館的錯誤觀念,讓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記錄佔領的點滴。在金鐘,有呼籲警察「請勿使用毒氣雙子」的模仿海報、貼滿便利貼的連儂牆,還有以雨傘為題的「雨傘人」和「百家傘」等等。
雨傘人
作為佔領區最初期的大型裝置藝術,「雨傘人」於十月六日被安放在政府總部旁的天橋下,後移至添美道入口,近連儂牆旁邊。這個無臉的人,由木板搭成,以繩子加固,看起來脆弱,但它站著的姿態異常挺拔,由白色小木塊做的頭昂首微微向天。他舉起右手,毫無畏懼地撐開黃色的雨傘。放在佔領區的中心,「雨傘人」堅定不移的姿態除了反映著佔領者的堅持,亦強化其精神象徵的作用,鼓勵各方的佔領者。另外,「雨傘人」更與裝置藝術的原意不謀而合。裝置藝術之所以放在室外,是希望藝術品能與週邊環境互相呼應,如柏林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它由一座座高低不等、棺木形的灰色水泥雕塑而成,讓人走在其中,靜靜悼念二戰期間被殺的猶太人,亦提醒後人戰爭之可怕。香港街頭不乏裝置藝術,例如旺角朗豪坊門外之雕塑,卻只淪為商場招徠,部份雕塑更常被遊人當作椅子。因此,「雨傘人」的出現與金鐘佔領區互相配合,既有守護佔領者的意味,亦與佔領者融為一體,真實呈現何謂裝置藝術。
百家傘
懸掛在政府總部天橋之間的「百家傘」,甫出現在金鐘佔領區時,實在產生一種讓人驚鴻一瞥的震撼。這藝術品的美麗之處不僅於其色彩斑斕,創作者背後的心思和迅速回應更讓人感動。記得十月初,佔領者剛適應佔領區席地而睡的生活,香港人亦從催淚彈的驚恐中醒來,政府依然未有正面回應市民,整個城市都沉默無語。就在那個時候,一群浸大藝術系學生以三日時間不眠不休收集和縫製這一幅「百家傘」。
我們用藝術形式延續「九二八」中破損雨傘的生命。一把把來自不同香港人的傘子,因為參與過同一場運動,就這樣被連結起來。抬頭一看,這些雨傘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可能你曾跟它們在街邊的小攤檔、某間便利店的貨架上相遇;或是你曾擁有一把相同的雨傘,可是從來沒有好好觀察傘子的另一面。透過縫製,這些被丟棄的雨傘不再孤單,反而因此成為另一個更大、更闊的帳幕,繼續保護留守的佔領者。同時,這三百把雨傘標誌著運動的開端,提醒各人當初站出來捍衛香港的初衷,更為香港人上了一課藝術課,看如何將已損壞的公民抗命物品轉化,成為活生生的歷史記錄。
旺角 - 關公的浪漫,守護旺角站
警方於金鐘施放八十七枚催淚彈後,旺角亞皆老街與彌敦道交界於九月廿九日凌晨變成佔領區,亦成為佔領運動中唯一非港島的區域。因地理和參與者因素,旺角佔領區的人流相對上複雜,他們大多不受金鐘「大台」影響,從而慢慢形成自家特色。位於十字路口的佔領區事實上是九龍交通中樞命脈,同時亦是旺角的「大台」,故此旺角站可算是最難駐守的佔領區。在禁制令生效前,旺角多次有示威者遭人襲擊,更有人曾圍困佔領者,對著眾多鏡頭前恐嚇非禮女示威者,甚至嘗試為自己隨身帶刀辯護而說出「榴槤乜乜乜」的妄語,因此旺角佔領區較為危險。與金鐘相比,市民選擇張貼標語到地鐵站入口外,或是馬路花叢旁,多以收集木板、巴士站牌作為路障。因衝突頻頻,旺角的佔領藝術品並不多,反而結合地區特色,衍生了關公像等擺設,取其保佑之意,令佔領運動頓時充滿民間信仰色彩。
關公
關公廟最初出現於彌敦道近旺角道路面,一幅關公像放在簡陋的卡板路障上。關公瓷像前有香燭台和酒杯,讓佔領善信隨時獻上祭品供奉。及後,有人以木板搭建正方形關公廟,令關公像無需日曬雨淋,外型與一般關公廟無異,惟放在風雲色變的旺角,對某些佔領者來說,供奉關公是一種安慰心靈的方法。在隨時被人攻擊的旺角街頭,以關公肅目的眼神、義薄雲天的精神來守護,可算是示威者對宗教的一種依賴。
在傳統中國民間信仰中,關公一向因其忠烈重情而備受尊崇,於歷代被視作保佑平安的神明之一。示威者經歷過「藍絲帶」攻擊後,擺設關公只因渴求安心平安,免受警察不合理暴力,更諷刺的是,有警察同樣會供奉關公,造成關公角色的矛盾局面。有示威者更在關公廟貼上標語,明言「關公不會保佑助紂為虐的警察」,又警告拆除關公廟會「褻瀆神明遭天遣」。如此解讀,當然只屬個別佔領者的看法,以力保佔領區不受影響。但當隨處可見的小型關公廟,被放在佔領區,以神明作為他們的屏障和示威用具,它隱約滲透出一份香港特色,展示民間信仰也可以成為一種抗爭藝術。
銅鑼灣 - 傘落崇光 香港重光
在三個佔領區中,銅鑼灣雖然佔領電車路等主要行車線,但因人數不多,亦較為平靜。由報章訪問所見,銅鑼灣佔領區集會由市民自發,會定時舉辦討論會商討方案,並有專人筆錄,氣氛融洽。因佔領者不多,以及範圍較大,銅鑼灣的藝術空間適合放置大型平面藝術品,如十月中軒尼詩道地上放置的七色巨型雨傘就是一例。此藝術品由一眾設計師和師生集體創作而成,利用數十把不同顏色的雨傘組成一把巨大的傘子,對抗胡椒噴霧。在巨傘的反襯下,用作驅散示威者的胡椒噴霧也立時變得渺小。雖然雨傘的力量有限,但只要它們集中在一起,傘後的人群就能團結起去抵擋無情的攻擊。而顏色繽紛的雨傘排列得宜,就像顏色轉盤(Colour Wheel)一樣,以多種色彩帶來希望。
若要從最佳角度觀賞七色巨型雨傘,必須從高處看下去,因其放在平面,所以於地面觀賞難免會削弱完整性。幸好銅鑼灣商場眾多,不少人能從靠窗的扶手電梯或是商鋪上俯瞰藝術品。雖說銅鑼灣因高級商場林立而為人詬病,卻因此令這個藝術創作在「地利」上佔盡優勢,讓更多遊人觀賞雨傘運動的藝術成果。
結語:你離開了卻傘落四周
在藝術史研究上,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是其中一個研究分支。物質文化強調透過仔細觀察物件特徵,從而反映當時情況,重構事實。對剛完結的雨傘運動,在資料收藏方面,已有不同媒體和市民以文字、相片、聲音,甚至錄像作記錄,這有助重塑佔領者和佔領過程的面貌,但就只有身處佔領區當中的藝術品才能真正突顯抗爭者雖心存恐懼卻迎難而上的精神。這一場覺醒,令香港藝術打破過去的展示形式,真正走入群眾之間。佔領過後,希望藝術品能妥善保存,成為精神圖騰去喚醒我們,二零一四年是香港人的政治啟蒙時代,也是一場藝術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