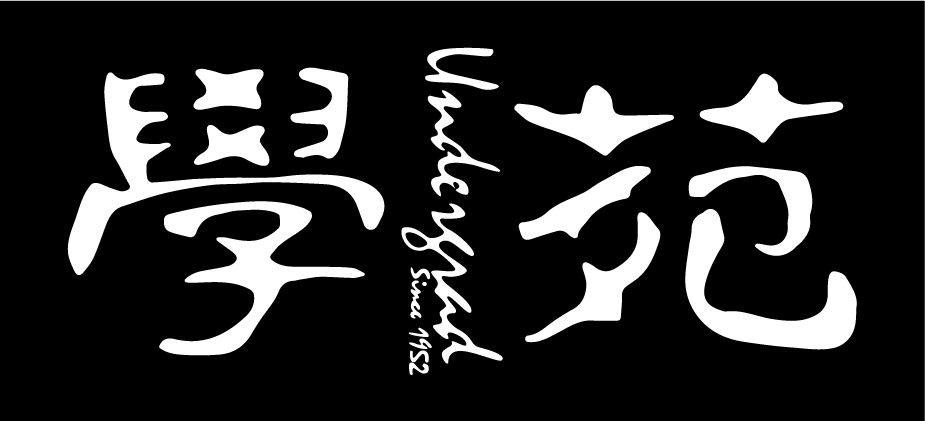文/去屆編輯 鄧梓明
2021年12月,為慶祝尖沙咀鐘樓鳴鐘一百周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為鐘樓加裝數碼鐘聲。啟動典禮上,鐘樓被燈照成紫紅色——活動的主題顏色,但沒有人在典禮上解釋,傳媒對此也隻字不提。一座意義不明的紫紅色鐘樓成為2021年詭異的城市景觀之一。此後,我們開始在尖沙咀聽到久違的鐘聲,鐘聲融入海濱,成為另一個我們習以為常的物事。鐘樓在詭異與尋常、無法理解與太快看見之間搖擺,我們可以如何重新看見鐘樓,如何聽見鐘聲的文化意義?
-3-512x341.jpg)
|鐘樓歷史:發展狂潮的倖存者
尖沙咀鐘樓曾為前九廣鐵路火車站的一部分。火車站於1916年啟用,鐘樓之時鐘和銅鐘於1921年安裝在鐘樓,開始報時。後來,鐘樓四面時鐘分別裝上摩打,但時鐘因此不同步,所以1950年起,銅鐘停止運作,現時放在鐘樓底層,途人可透過窗戶一窺銅鐘面目。
五六十年代,火車站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常見千人長龍,乘客或到新界郊遊掃墓,或轉乘至中國和歐洲。1955年起,粵籍香港居民每次赴粵前,都須在站內申請邊境通行證,更加劇排隊苦況。1961年清明節,工商晚報寫道:「清晨六時,已有數千人披星戴月,雲集九廣路車站⋯⋯六時後,赴和合石之男女,已排隊至半島酒店前。而赴沙嶺之人龍,則伸入廣東道。」
-512x341.jpg)
同時,火車站設施開始落後,尖沙咀空間亦漸趨飽和。車站附近地段繁忙,不容擴張,故搬遷火車站勢在必行。1960年1月,政府宣布將尖沙咀火車站遷往紅墈,當時社會大致同意拆卸火車站,只有零星聲音支持保育。70年代,民間支持保育火車站的聲音開始壯大。分別服務外籍人士和華人的九龍居民協會和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先後為此去信政府;《南華早報》偶有讀者來信提出活化構思,建築師學會亦曾撰文分析活化可行性,即引來讀者來信附議。
但這些人士往往遇上鐵板一塊——多個政府決策部門由始至終無意保育火車站。城規會早於60年代的用地規劃中便計劃拆卸火車站,改用地為開放空間,市政局則在1972年決定在火車站原址興建文化中心。1976年,城規會讓步,將火車站大樓用地由開放空間改為社區用途,為文化中心開綠燈,火車站的命運開始倒數。
1977年,香港文物學會應運而生,並向港督請願保留火車站:車站大樓隨時可活化成大會堂,比興建文化中心耗時更短,花費也不高;火車站大樓是香港地標,有歷史、建築及情感價值;若妥善規劃,尖沙咀海濱有空間同時容納文化中心及火車站。政府拒採納學會意見,稱九龍急需文化設施,但火車站無法轉型成音樂廳等高規格的文化設施;文化中心合適地點難覓,重新設計亦需時兩年。學會翌年收集到一萬五千個聯署,向英女王請願,同被駁回。
除了聯署,文物學會亦獲得不少專業團體和社區組織支持,甚至政府內部亦不乏反對拆卸的聲音,在1977年剛成立的古諮會也建議保留大樓部份外牆,但其餘社會大眾真的在意火車站大樓嗎?雖然一大部分聯署來自各行各業的華人,但英國官員似乎不予理會,與文物學會開會時引述社署意見稱,華人會出於禮貌而簽名打發聯署義工,故聯署不代表真實民意。該官員又稱自己在港訪問了兩百人,其中多為華人,雖有人希望保留鐘樓,但每一個人都說不希望保留火車站大樓;學會成員皆表懷疑。市政局民選議員黃夢花亦指其接觸的華人中,多對拆卸火車站沒有強烈意見,而文化中心能提供活動空間,正好切合公眾所需。本地報刊持不同立場,例如《華僑日報》和《南華早報》認為火車站毫無保留價值,應連同鐘樓一併拆卸;《星島晚報》認為拆火車站無可避免,但相信多數市民不贊成拆除鐘樓;亦有小報社論建議將火車站活化成大會堂、博物館或藝術館,以保留一棟在九龍已所剩無幾的特色建築。當年的大眾輿論已難以考究。
1978年,火車站大樓被拆卸。但在古諮會之請求下,市政局同意保留大樓外牆的花崗岩圓柱。五年後,火車站的六條十一米高的古典圓柱在尖東的市政局百週年紀念花園內重置。銅鐘則前後被遷至多處,直至2010年,九廣鐵路贈銅鐘予政府,銅鐘方於鐘樓展出。
-512x384.jpg)
2021年末,鐘樓塔頂首次播出數碼鐘聲。康文署指,鐘樓原本中通,但拆卸火車站後鐘樓結構受影響,政府須以混凝土加固樓面,將鐘樓分成幾層,即使最終能將銅鐘放回鐘樓頂樓,聲音亦不如以前。因此,署方找到同一型號的「姊妹鐘」,重新錄製銅鐘聲,透過鐘樓頂設數碼播放系統,與天文台時間同步,準時報時。
鐘樓處於文化中心發展藍圖以外,因而得以保留。倘若對岸的皇后像碼頭象徵著無視保育和文化、固執無情的都市發展思維,那麼電子鐘聲則象徵著主動的保育嘗試——只要不妨礙發展,政府願意用虔誠的心克服困難,重構歷史和文化。鐘聲或是優雅的反抗:當發展巨輪碾碎火車站,鐘聲就這樣輕輕地飄出來(噹!)。鐘聲或也是諷刺的:銅鐘為何不能鳴響?正是因為碾碎了火車站,而建了一棟名曰「文化」的中心!
|聽見鐘聲、看見鐘樓
文化評論家Ackbar Abbas批評文化中心「是現代主義的無特色結構之一,可以來自任何地方,看似一個巨型滑雪場」,而現代的文化中心與古典的鐘樓相毗鄰,構成令人難以理解的景觀,是最露骨的不諧和斷裂。這種視覺上的極端不協調,本可以令鐘樓以一種奇異的姿態攫取途人的目光,強迫途人洞悉其背後的歷史,成為成功的保育,但事實上鐘樓卻輕易地融入了四周。Abbas評論道:香港發展過急,香港人失去了時間和歷史的感覺,新和舊可以同時存在。鐘樓輕易地融入文化中心,亦淪為可供輕鬆消費的裝飾品,成為一種「供視覺消費的歷史圖像」;當表面的歷史被人看見,其歷史痛苦的部分便會消失。這是庸俗的保育,是必須警醒的懷舊。
於是,鐘樓重塑歷史:濾去不愉快的記憶片段,留下快樂、庸俗的懷舊。我們看見鐘樓的宏偉、看見上世紀偉大的鐵路歷史,在文化中心旁沉浸在古典建築的美學,因此忘記歷史裡的長龍和抗議,也對鐘樓上下部份紅磚顏色的差異不以為意——它們是因拆卸火車站而添的新磚。
這麼悲觀嗎?文化理論家Svetlana Boym在《懷舊的未來》則以另一方式理解懷舊,將其區分成二,其中修復型懷舊渴望還鄉,回到美好的過去。「過去不是某種延續,而是一個完美的快照。而且,過去是不應該顯露出任何衰敗跡象的;過去應該按照『原來的形象』重新畫出,保留永遠的青春氣息。」自1950年起,鐘樓不再敲鐘,2021年響起的電子鐘聲是完美的快照,卻也是斷裂的記憶。誠如政府新聞稿所言:「讓原只屬於祖父輩的珍貴回憶,成為一代又一代美好的記憶。」——在此,懷舊更貼近「復古」。
在快速變革、記憶多有斷層的時代,我們對保育的想像是不是只能如此?我們是否只能依靠如幻似真的科技,強行復活逝去的舊事舊物,拼貼出一幅金黃色的陌生記憶,讓我們快樂地蕩漾其中?政府請來歷史學家為電子鐘聲拍片宣傳,卻只是緬懷過去;舉辦鐘樓趣史講座,半點不談保育運動;Facebook帖文引用文物學會當年的請願信,卻只是讚嘆火車站的典雅宏偉,好讓我們「發思古之幽情」;趣聞軼事、古色古香之外,別無其他。鐘樓輕飄飄,沒有過去,沒有重量。不是這樣的。我們還可以認真地面對歷史,直面那些不有趣也不生動,甚至令人不適、催人反思的歷史。
-1-512x340.png)
Boym因此說懷舊可以有未來。第二種懷舊是反思型懷舊,我們明白過去不可返回,於是在懷想過去的同時也保持一種反思的、諷喻的距離。伊甸不斷延宕,懷舊者也因此有空間批判地挪用記憶碎片,為當下注入活力:創造什麼記憶取決於人的閱讀。若我們仔細看,便能發現這場保育背後的戲謔:六條古典圓柱被隨手丟到一公里外的紀念花園,無意尊重圓柱的承托支撐功能,亦無意配合周遭環境。鐘樓被硬生生分成三部分——鐘樓、銅鐘和鐘聲。銅鐘脫離了專屬它的頂層,靜靜地放在鐘樓底層,甚至不是掛著,而是被以往鐵路使用的枕木架起,通過窗戶受人瞻仰。鐘聲更如鬼魅,不知哪裡飄來,反正不是這銅鐘。銅鐘、窗戶、鐘聲便合成一個無意的玩笑,成為我們欲創造一個庸俗的共同記憶時的挑釁、反抗——它自揭傷疤,強迫途人發掘它背後的保育歷史。當我們在腦海裡創造一幅一個世紀前繁忙而恬靜的火車站圖畫,那鬼魅般的鐘聲或可撕開一條裂縫,那幅可輕鬆消費的歷史幻象也無從產生。2021年前,我們還可輕易無視鐘樓的故事,現在電子鐘聲響起,以一把不屬於鐘樓的聲音哀悼銅鐘,我們再難來去自如。
Boym筆下反思的懷舊者,重視時間的延綿,當我們被植入古舊的記憶,錯置到這「經過了修葺,美化得面目皆非」的斷裂時空中,我們便要重奪屬於我們的歷史,為那座被迫沉默的鐘樓——為我們——說話。如果當年的保育工作可以做得更好,就讓我們永遠記得一座沉默的鐘樓吧。如果當年實難平衡發展和保育,就讓我們誠實地聆聽發展的代價吧。
編按:本文原定於二零二三、二零二四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輯委員會任內出版,惟因編輯自身能力不足而未竟。敝編委會邀請去屆編輯續筆完稿並予刊載,冀此能成引玉之磚,為社會思潮添一磚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