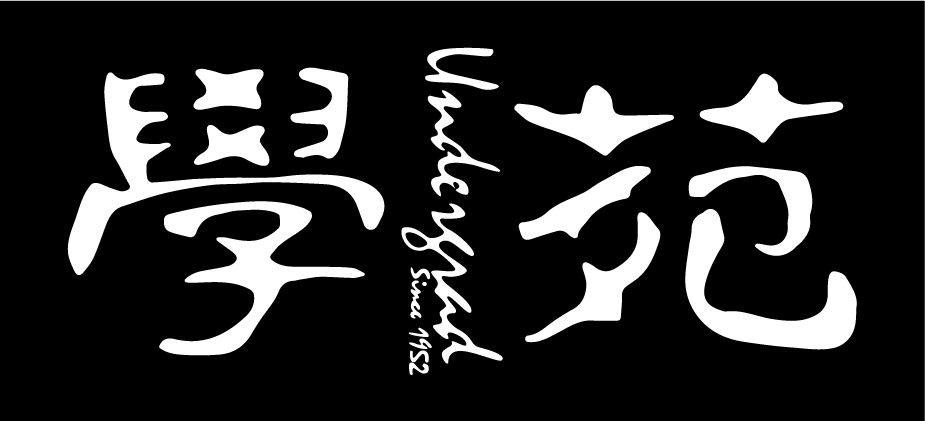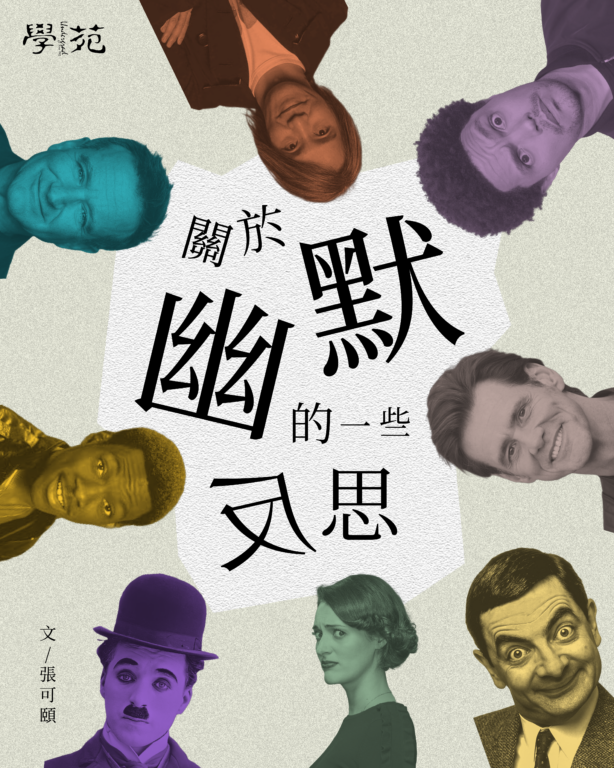
文/張可頤
我們見人踩屎偷笑、見街舖食字好笑、看卓別林電影笑中帶淚、聽地獄gag難忍爆笑,不時笑到爆肚,腸啊、心肝脾肺腎全跌出來,仍一邊撿回肚子裡的內臟,一邊笑。搞笑作品在我們的文化中佔據重要地位,周星馳、黄霑、昆汀.塔倫提諾的作品都多多少少因搞笑成名。這些笑的來源分很多種:有的笑位由古怪的行為動作或結果與預期的反差造成,比如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四大才子在橋上追逐呼喚美女「秋香」,其背影頗為動人,惹得觀眾浮想聯翩,結果秋香一轉頭,卻是滿臉鬍渣且正挖著鼻屎的女裝大叔;有的笑位卻較矛盾,《年少日記》中鄭中基飾演的角色對學習成績稍遜的大兒子頗嚴厲,一場景中大兒子向媽媽遞水稱:「a cup of water」,鄭中基立即糾正:「唔係a cup of water,係a glass of water先啱,垃圾!」筆者見此情境即刻笑了,但與看見秋香的大笑不同,是一種不自覺的苦笑。因著不同搞笑方法造就的笑有何不同?當我們以「幽默」或「低俗」等字眼形容引人發笑的言語行為又好像暗示著笑話實有層級之分,這又是為什麼?

|三種對笑的看法
哲學家John Morreall精煉了對笑及幽默的三種論點:優越論、壓抑後之釋放論、不協調論。
因自我優越感而生的笑自柏拉圖《理想國》就被提起,其指笑是一種「莫名的激情」,我們因為自身莫名的觀念而猛然產生的「榮耀感」而笑。此種觀念,是民族環境偶然造成的,若男性以肌肉健碩、身材高大為優越,體型高大健碩的民族就會嘲笑身材較矮小的民族。優越感也會從自己曾克服過的軟弱而生,曾遭嘲笑身材矮小的人經青春期突然長高後,亦會笑其他身材矮小的人。
柏拉圖指,與他人的軟弱作比較,是「認識自己」的相反。只有忽略歷史環境之偶然者,才會高估自己的能力。嘲笑他人身體孱弱者,稱自己全憑努力才打造一副健碩身材,質疑孱弱者為何不努力健身,笑其風一吹便倒。殊不知此舉忽略了天生基因、家庭經濟條件,及繼而能承擔的營養、健身服務之不同。笑他人者認為自身努力是決定結果的關鍵,實情並非如此。這是種因滿目無知而生的邪惡。高估自己而蔑視他人的笑,在理想國中是被禁止的。
壓抑後之釋放論解釋發笑的心理機制。我們會產生並積累各種情緒能量,只有特定場合才會被觸發。正如一位母親眼見孩子徒手爬山坡,卻不慎滑落,弄得一身髒,正準備生氣大罵時,孩子拿出一朵花。原來孩子爬山是為了摘花給母親,母親以笑釋放壓抑的情緒。這解釋了一種放鬆的笑,當本來的情緒失落於原訂目的,故自然地釋放。
|不協調論
當我們與他人交流時,通常都會根據常識預設對話將如何發展,但當我們的期望與實際情況不協調,就令人產生古怪的感覺且發笑。比如:一名醫生說:「阿明,只是一場小手術,不要緊張。」病人答:「醫生,我不叫阿明。」醫生答:「我的名字叫阿明。」
《On Humour》一書的作者Simon Critchley分析,不協調論是基於敘述者與聽者的互動關係,牽涉彼此之間對意義的認知。當我們與他人說笑時,話語或呈現出來的畫面是否好笑,基於我與他是否共享對事件的認知。若認知契合,搞笑便自然地誕生。換言之,是否能創造出笑話,選擇對的聽眾是重點。可見,在Critchley眼中,講笑需借助一個共有的社交世界。這是一種需共同合作,才能成功玩下去的遊戲,是冥冥中的契約關係。
講笑的契約關係還包括「知道他正在講笑」的意識。假如有人和我講一個笑話:「我以前喺動物園返工,當時嘅工作係扮馬騮⋯⋯」要形成一個笑話的首要條件是我得先意識到「他正在和我講笑話」。如果我打斷他的說話,或者中途離開,讓這個笑話不能形成,那麼原本的笑話契約就會被打破。
「蕩下蕩下,我唔小心蕩咗入隔離嘅老虎園,當時真係好驚⋯⋯」當敘事者不斷鋪墊,我和他交流中屬於緊張或期待的橡皮筋不斷拉伸,「老虎走過來說:『唔使驚,我係小明啊!』」當最後的punchline出現,橡皮筋突然鬆開,緊張感徹底消失,便會產生一種放鬆、快樂的情感,笑容應運而生。
可見,對話中的搞笑講究概念的轉換及文句修辭效果。簡練易懂的話語及對時機的把握造就笑,Critchley稱之為靈魂中的智慧。不過,擁有這種智慧的關鍵在於能否抓住聽者的靈魂,講笑者有意說笑,但如何鋪排修辭讓聽者明白,乃至投入;如何選擇轉換原本敘述的概念的時機,都十分重要。
事實上,這也顯示了你和聽者的關係。若你有意博人一笑,就需要配合他的認知,創造出與他原本認知事物的不同一面,以營造古怪搞笑感。但當你和聽者,原本就共有一套對事物的認知和觀念,你便不需刻意迎合他人,笑如清風閒雲自然而來。這是判斷「朋友」的標準之一,當你和朋友共享類近的道德觀念、對事物的判斷,你們對好笑與否的判斷也會相似。
|笑於人之意義
有人指,與貓狗玩耍時,其下巴微張,面容放鬆,好似微笑。但寵物不會嘲笑、冷笑,因為這類笑背後暗藏人的自我意識。哲學家Helmuth Plessner指出,笑證實了人類在自然世界中的反常地位。動物的生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牠們只是活著及經歷世界。而人類經歷的不僅僅是世界,我們還能經歷我們的經歷。人類對其經驗乃至自身有所反思,讓我們得以與直接的經歷保持距離,脫離日常生活,實現與自然的決裂。
我們用存在(being)來定義生物的一種狀態:我們會稱人類存在著,動物存在著,我存在著。但人類並非如動物般,只是受軀體驅使地存在,我們擁有(having)身體。「存在」與「擁有」兩個概念劃分人禽之辨。在經歷疾病時最能感受此情況,我們會有意識地認為身體的痛只是皮肉之苦,與精神上的痛苦有所不同。最明顯的經驗或是厭食症,此時我的身體徹底成為我所擁有的客體,而意識成為主體。而人類之所以反常,就是擁有這等反思能力。一但我思考,我恍如置身異鄉,我對自身變得陌生,自己與周圍有著無盡的謎團等我探索。
存在及擁有,我們可以藉此判斷一個笑話的高低。Critchley認為,大多數的喜劇是「尋求認同的喜劇」,只求找到觀眾的共鳴處並重複加強其共識,絕非試圖反思既定秩序或改變社會處境。此等喜劇不求變,反以一種相當平易近人的迷人手法鞏固現在的社會制度。導演王晶乃此類喜劇導演中的表表者:《精裝追女仔》中三名男主角為討好同一位女生而各買一至二百箱收縮水。一男主角以收縮水浸浴,面容、肢體扭擰捲曲,蹲走出浴室之際撞見一老婦,老婦見狀大叫「怪人!鹹濕怪人!」其後,警察趕到。情急之下,男主角佯作癲癇,配以悲情音樂歌舞一場。鏡頭轉向備受感動的警察及老婦,皆淚流滿面,逐放棄拘捕男主角。
這是一部純粹取悅觀眾的喜劇,在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並不少見。觀眾取笑三名男主角傻,為得到女人而失去理智;亦利用社會對女性及傷殘人士的偏見,引觀眾作笑。這種笑來自上文所述的優越感,覺得搞笑,實則是處於高地嘲笑弱者。這種笑,是身體的失控,是自主意識喪失身體控制權。笛卡爾在《靈魂的激情》第124條中闡述了這一點,笑在於這樣一個事實:血液通過動脈從心臟的右孔流出,使肺部突然且反覆地膨脹,導致它們所含的空氣排出,在喉嚨中形成口齒不清且爆炸性的話語;空氣從肺部衝出,帶動從胸到頸部的所有膈肌的運動,從而引起面部肌肉的運動。Helmuth Plessner稱之為「人與身體之間的斷裂而導致自我控制的喪失」。這等笑,是身體爆發式的表達,器官不停地震盪,這一刻不受我們控制。這也是為什麼有時大笑完腹部疼痛的原因。換言之,這種因緊張情緒不斷積累且迅速戳破而引起的短暫身體快感不一定有益。社會的無形枷鎖仍在,受傷的仍是社會中的弱勢。當聽到這等笑話,每笑一次便加固一次這枷鎖,對特定人或物的刻板印象更為加深。

而怎樣的笑話才能達至幽默境界呢?
Critchley說幽默應是一種關乎思想解放或拓闊視野的表達形式。一個真正的喜劇人,敢於看到世人一直迴避、害怕看見的內容。他所見的是關於人的處境,關於人們心底的恐懼,關於真相。一個幽默的笑話,不僅釋放身體的壓抑情緒,更為人們帶來解放,讓他們看見真相,進而有改變現狀的可能。查理.卓別林就是這樣的喜劇人。電影《摩登時代》中,卓別林飾演工業時代下的工廠工人,其搞笑場景是圍繞、展現當下時代的荒謬之處。普通工人如大齒輪下的小齒輪,不斷做重複的工作,但卓別林所演的工人卻作出超乎尋常的舉動⸺在流水線上不斷重複扭螺絲的動作,導致放下螺絲批休息時仍不自主地重複動作;看似滑稽地在廁所點煙,下一秒就被遠程監控著員工一舉一動的老闆在大銀幕中喝斥。這種幽默重現了工人的境地,將其超現實化,誇大地設想未來科技發達的社會中工人的處境,再將其呈現出來讓世人看見。

幽默在Critchley眼中的作用並非治癒或者拯救,幽默不會把我們從這個世界中拯救出來。反之,它逼迫我們看清、承認這個世界是不完美的、荒謬的,把我們從一廂情願的幻想之中狠狠地拖拽出來,像是逼迫洞穴中的囚犯面對陽光一樣,得到伴隨著刺痛的實相。幽默的笑話時刻提醒我們接受自己的狹隘,逼迫我們面對現實處境,所以幽默不令人忘我大笑,因幽默而來的笑是微笑。
Plessner稱微笑是心靈默劇,只有我們和所見之事物保持一定距離地審視和思考,才能看出其荒謬之處,從而發笑。所以這種笑是受自我控制的,微笑中含有的是克制與謹慎。卓別林預想引發的未必是徹底失控的捧腹大笑,而是由見到滑稽動作而來的大笑慢慢隨著工人景況的展示轉變為非直覺、因思考而來的微笑,進而難以發笑,因為觀眾看見的是不人道之環境所導致的悲慘境況。這種極度微妙的表達處於存在與擁有之間,這種微笑又嘲笑著人類處境的種種限制,這是幽默的本質,也是人類的本質:我們一方面擁有動物本能,見到古怪事物不禁大笑;另一方面卻能理性地控制自己的笑,兩者不斷拉扯,令人成為最憂鬱卻也最樂觀的動物。我們微笑著發掘自己的可笑。